一环
这是今早梦到的一篇文章。醒来时,情节还有些恍惚,像是走在一场大梦的边缘。我及时记下梗概,借AI之手,将其补全成篇。
一
那天出门的时候,阳光很好。
我走在前面,她跟在后面,隔着两三步的距离。这是我们习惯的位置,很多年了,一直如此。她走得轻,几乎不踩出声响,脚底像是抹了层软底的布,落在地上只有风穿过叶隙那样的动静。小时候我总觉得这是她做姑娘时养成的习惯——她说她们那一辈人,走路要轻,说话要细,不能惊着什么。后来我也就信了。
我们要去找一片山林。什么样的山林,我说不上来,只觉得该是青葱的、安静的,最好有一条溪水,从山腰绕下来,绕一个弯,再绕一个弯。她说她知道这样一个地方。
出门时经过堂屋的角落,那里放着一个旧木箱,箱盖上摊着几本发黄的册子,最上面那本日记本的封皮已经脱落了一半,露出里面灰白的衬纸,颜色和堂屋墙上她的照片相近,照片里的她比现在年轻。她忽然停住了,目光落在那本册子上,停了几秒,又好像不止几秒。
我走出几步,回头看她。
“怎么了?”
她没回答,只是站着,像是在辨认什么,又像是在确认某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。阳光从窗户斜进来,落在木箱上,落在日记本上,也落在她站着的地方。我低头看去,地上只有我一个人影。
“外婆?“我叫她。
她回过神来,目光从那本册子上收回,轻轻摇了摇头,像是要把什么念头从眼前挥走。
“没什么。“她说,“走吧。”
她跟上来,依旧是两三步的距离,依旧没有声响。我们走出院子,沿着村路往山的方向去。风吹过路边的草尖,她走在我身侧,头发被风掀起一角,又落下。
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她最后一次出门。
我不知道那天我们走了多久,只记得阳光一直很好,好得让人有些恍惚,像是走在一场大梦的边缘。
二
我们走出院子十几步,我忽然停下来。
“外婆。“我转过身看她。
她站住了,隔着那两三步的距离,站在风里。她的头发灰白,被风吹起来,露出额头的几道皱纹。她的眼睛望着我,不说话。
“刚才那本册子,“我说,“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?”
她沉默着。风吹过路边的草,沙沙地响。远处有人在喊什么,声音被风扯得很远,听不清。
“没什么。“她说,“都是老早的事了。”
“你停了好几秒。“我说,“你看着那本册子,像是……像是见到了一个很久没见的人。”
她没接话。我看着她,她也看着我。这样对视了一会儿,她忽然笑了一下,很轻,像是一声叹息落在地上。
“你眼睛倒是尖。“她说。
她转过身,往回走。我跟在她后面,依旧是那两三步的距离。我们回到堂屋的角落,回到那个旧木箱前面。她伸出手,悬在那本日记本上方,悬了几秒,然后轻轻翻开封皮。
日记本里夹着几张纸,折着,边角已经磨损发毛。她抽出其中一张,展开。那是一张泛黄的清单,墨迹晕开了一些,但字迹还能辨认。纸张很薄,像是那时最便宜的那种,摸上去有一种脆的质感。
“这是那年写的。“她说,“三十四年,还是三十五年,我记不清了。”
我凑过去看。清单上列着一些物资的名字——粮食、布匹、药品,还有一些我认不出的东西。每一项后面写着数量,有的旁边还有一个签名,字迹潦草,像是匆匆写下的。最底下有一行小字,时至如今还比较清晰,写着"环线第三站交接”,后面是一个名字:阿椿。
“阿椿是谁?“我问。
她没立刻回答,目光落在那个名字上,像是在辨认,又像是在回忆。过了一会儿,她说:“一个老乡。当年一起做事的。”
她把清单递给我,手指碰到了我的手背。那一碰很轻,几乎感觉不到温度。
“路上跟你说。“她说,“走吧,再去那片山。”
三
我们沿着村路往山的方向走。
路两边的田刚翻过,土块堆成垄,有人在远处弯着腰,不知道在做什么。风吹过来,带着土腥气和草叶被晒热的味道。她走在我前面,步子不大,但很稳,像是走过这条路很多次,闭着眼睛都能认得。
“那年我十九岁。“她忽然开口,声音不响,像是对自己说的,“还是二十岁?记不太清了。反正就是那个年纪,什么都不怕,觉得天塌下来有更高的人顶着。”
我加快几步,走到她身侧。她没看我,眼睛望着前方,像是在看一条只有她能看见的路。
“这张清单,“她指了指我手里的纸,“是在路上写的。”
“什么路?”
“环线。“她说,“一条山路,绕着这片山走一圈,把物资送到各个点。一个来回,快的话三四天,慢的话五六天。我们那时候走的就是这条线。”
我低头看那张清单。纸张发黄,边角磨损,墨迹晕开了一些,阿椿的名字变得有些模糊,但还能辨认。粮食、布匹、药品、数量、签名,字迹潦草,像是匆匆写下的。
“阿椿,“我念出那个名字,“他是做什么的?”
她停了一下,脚步没乱,只是沉默了片刻。
“向导。“她说,“本地人,路熟。哪条道能走,哪条道不能走,哪条道日本人来过,哪条道他们不会来,他都知道。他带着我们走,一个点一个点地送。”
“后来呢?”
她没回答,继续往前走。我跟在她后面,看着她的背影。她的衣服被风吹得轻轻鼓起来,像是身体里没什么重量,只是被风撑着。
“有一段路我没走完。“她说,“走到一半,发了高烧,走不动了。阿椿让我在山洞里歇着,他带着其他人继续走。他说,你等着,我们走完这一圈就回来接你。”
“他回来了吗?”
她没说话。
我们走了一段,她才开口,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,像是怕惊着什么。
“没有。“她说,“他们走的那一段,后来出了事。具体什么事,没人说得清。有人说遇到了巡逻的,有人说走岔了路,有人说……反正就是没回来。”
她停下脚步,抬手指着前方。
“你看,就是那片山。”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。远处是一片青葱的山林,山势不高,但很密,树木连成一片,像是把什么秘密藏在深处。一条小路从山脚绕进去,绕一个弯,看不见了。
“环线就是从那里进去的。“她说,“一个圈,绕一圈,再从另一边出来。我走的那一段,是前半圈。阿椿走的那一段,是后半圈。”
她顿了一下,声音低了下去。
“那一圈,我没能走完。”
四
我们沿着小路往山里走。
林子越来越密,阳光被树叶筛成碎块,落在地上,落在草叶上,落在我和她走过的路上。风从树梢穿过来,带着湿气和一种青涩的味道,像是刚下过雨,又像是雨要来了。
“阿椿长什么样?“我问。
她走在前面,步子依旧很轻,脚底几乎不踩出声响。她没回头,只是说:“很普通的一个人。瘦,黑,话不多。但眼睛很亮,看人的时候,像是能看透你心里在想什么。”
“他多大了?”
“跟我差不多,也许大个一两岁。也没人问过他,那时候谁管这些。“她顿了一下,“他有一个妹妹,在另一个队里,做缝补的活。他总说,等打完仗,要回去看她。”
我们走了一段,她在前面忽然开口,声音像是被林子里的风吹散了一些,有些飘。
“有一回下雨,我们躲在山洞里。雨下了大半夜,我们就在洞里坐着,等天亮。阿椿坐在洞口,望着外面的雨,不说话。我问他想什么,他说他在想那个圈。”
“什么圈?”
“环线。“她说,“他说,这条线,像一个圈,绕一圈,又回到原点。我说,那不是很好吗,回到原点,就不怕走丢。他笑了笑,没接话。”
她停下来,站在一棵老树旁边。树的根部有一个凹进去的洞,积着一些枯叶。
“后来我才知道,他说的’回到原点’,不是那个意思。“她说,“他的意思是,有些人走完一圈,就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我没说话,只是站在她身后,看着她的背影。她的衣服很干净,像是刚换过的,但颜色很旧,是一种褪了色的灰蓝。风吹过林子,树叶哗哗地响,她的头发被吹起来,露出后颈。
我低头看手里的清单。墨迹晕得更开了,阿椿的名字变得愈发模糊,像是被水化开的影子。我的手是干的。
“走吧。“她说,“前面就是了。”
她转过身,继续往前走。我跟在她后面,依旧是那两三步的距离。林子越来越深,光线越来越暗,她的背影在树影里忽明忽暗,像是要融进什么里去。
我伸出手,想要拉她一把。我的手正在穿过她的衣角。我什么也没触到。
五
林子到了尽头,豁然开朗。
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山坡,草长得齐膝高,被风吹得往一个方向倾斜。远处是连绵的山脊,近处有几棵孤零零的树,树冠很大,投下一片阴影。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,落在山坡上,像是一层薄薄的金。
她站在林子的边缘,没有往前走。
“就是这里。“她说。
我走到她身边,看着眼前的山坡。风吹过来,草浪起伏,像是一大片绿色的水。有几只鸟从草丛里飞起来,扑棱着翅膀,往山脊那边去了。
“你当年走到这里,就停下了?”
她点了点头,抬起手,指着山坡的另一侧。
“阿椿就是从那边走的。那天早上,我的烧还没退,站都站不稳。他说,你在这里歇着,我们走完这一圈就回来。他说,这条线,绕一圈,回到原点,你就在原点等着。”
她放下手,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等了三天。“她说,“三天之后,有人从另一个方向过来,把我接走了。他们问我其他人呢,我说往那边走了。他们去找,什么也没找到。”
我看着她,她的眼睛望着远方,像是在看一条只有她能看见的路。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?“她笑了笑,很轻,像是自嘲,“后来我老了很多年,问了很多人,走了很多地方,那条环线的后半段,始终没走完。阿椿,还有那些跟他一起走的人,就这样不见了,像是被山吞了。”
她蹲下来,伸出手,悬在草尖上方,没有碰到。
“这一圈,我没能走完。“她轻声说,“少了一环。”
我站在她身后,看着她的背影。风吹过山坡,草浪起伏,她的衣服被吹得轻轻鼓起来。
“所以少了一环啊。“我说。
她没动,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是啊,少了一环。”
我们站在那里,不知过了多久。阳光慢慢偏西,云层聚拢又散开,风从山脊那边吹过来,带着一种凉意。
她站起身,拍了拍衣角。她的手穿过衣角的布料,什么也没拍到。
“以后就把我安葬在这吧。“她说。
我愣了一下。
“在这?”
“嗯。“她望着山坡的某个方向,像是在看一处只有她能看见的地方,“这里很好。安静,有风,有草。阿椿当年就是从这里走的,我留在这里,离他近些。”
“可是——“我顿了一下,“少的那一环怎么办?”
她转过身,看着我。她的眼睛在夕阳的光里,有一种很淡的笑意。
“我已经实现不了了。“她说,“那条环线的后半段,我这辈子是走不完了。但你不一样。”
她伸出手,悬在我面前,像是想拍我的肩,却停在半空。
“下次你来的时候,替我走一走。“她说,“走完那一环,回来告诉我。”
我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其实她已经在那里了。
她笑了,很轻,像是一声叹息落在风里。
“走吧。“她说,“天快黑了。”
六
我又去了那片山。
是什么时候去的,我说不太清。是后来,还是刚才?不清楚。只记得那天阳光也很好,像我们出门的那天一样。但我也分不清哪一天先发生。
我一个人走在那条小路上,林子依旧密,阳光依旧被树叶筛成碎块,落在地上,落在草叶上。风吹过来,带着湿气和青涩的味道。
我走完了那条环线的后半段。
路比我想象的要长,也比我想象的要难走。有的地方已经荒了,长满了荆棘和野草;有的地方被人踩出了新路,绕过了原来的弯。我一边走,一边记,记下每一个转弯,每一棵老树,每一条小溪。我用手机拍了一些照片,有的拍得清楚,有的拍得模糊。我捡了一片叶子,夹在口袋里。
走了多久?也许是半天,也许是一天。我走到环线的终点,那里是一个废弃的山洞,洞口长满了藤蔓,洞里空空的,什么也没有。我站在洞口,望着里面,想喊一声阿椿的名字,又觉得没必要。他早就不在了,喊了也没人应。但我还是喊了。当然,无人应答。
我回到原点,回到那片山坡。
山坡上已经立着一块石头。
我认得那块石头。她的碑。
碑不高,是那种最普通的石碑,灰白色,表面有些粗糙,像是被人匆匆刻出来的。碑上刻着她的名字,字迹不深,但能认出来。没有生卒年,没有其他字,只有她的名字,孤零零地立在那片草浪里。
我站在碑前,站了很久。风吹过山坡,草浪起伏,几只鸟从草丛里飞起来,往山脊那边去了。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,落在碑上,落在我的肩上。
我低头看手里的清单,纸张已经很旧了,边角磨损发毛,墨迹晕成一片。阿椿的名字早看不清了,像是一个被水化开的影子。我的手还是干的。或者说,它该被打湿了。
我把清单折好,放在碑前。又从口袋里拿出那片叶子,放在清单上。
我抬起头,望着远方。远方是那条环线的方向,山林连绵,看不见尽头。我在那里走过,一个弯一个弯地走过,走完了她没能走完的那一环。
我收回目光,看着那座沉默的碑。
“这一环,我给您带来了。”
风吹过山坡,草浪起伏,碑上的名字在夕阳里泛着很淡的光。我站在那里,又站了很久。阳光慢慢偏西,云层聚拢又散开,天边的霞光一点一点暗下去。
我没有再看身后的影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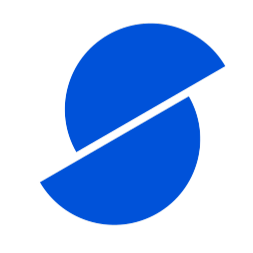 Spixed's Blog
Spixed's Blog Spixed
Spix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