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章
谨以此文,作为十八岁的序章,致敬那些在沟渠里仰望过的星空,和那些在沉默中震耳欲聋的成长。
若故事与现实有出入,请视作平行世界里另一种可能的运算结果。
…………
晚十点半,直播课结束的提示音像一颗石子投入深井,在体内激起一阵沉闷的回响。我摘下耳机,耳廓因为长时间佩戴而微微发烫,那是现实残留的余温。
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动了一格。那一瞬间,我切断了与外界知识链接的脐带,鼠标滑向那个熟悉的图标,熟练地接驳进另一个维度。显示器黑了一瞬,随即亮起,《崩坏:星穹铁道》的登录界面像某种夜行生物般浮现。屏幕的冷光如潮汐般涨起,将我那张略显苍白的脸,漂白成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。
一百三十多抽。又是大保底。
我不信邪地点击鼠标,星轨滑过,依然是刺眼的紫色。没有金光。这个数字像某种嘲弄的暗号,标记着我与概率之神之间单方面的失约。在赛博星海里,我是那个总是慢半拍的“流亡者”;在名为高三的现实战场上,我能精准地推导每一个公式,却唯独缺失了某种名为“共振”的天赋——我能与周围维持长久的通话,却总感觉自己像一个信号延迟的老式接收器,在他们热切交换的新梗与爱好之外,孤独地捕捉着过时的频率。
……
门外传来拖鞋摩擦地板的沙沙声。那特定的频率,属于母亲。
整个过程流畅得近乎一种生存本能——Alt + Tab 极速切换,原本浩瀚的星系瞬间折叠进后台的黑暗,屏幕上无缝衔接出一张写满笔记的 PDF 文档。放在键盘上的手抽走,指尖在空中悬了一瞬,随即有一搭没一搭地点着桌面,脊背微微佝偻,面部肌肉迅速从紧绷切换至一种“苦思冥想”的松弛。
门被推开一条缝,光线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切了进来。
“还在学啊?”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,带着小心翼翼的欣慰,“给你热了杯牛奶,喝完早点睡,别太拼了。”
“嗯,看完这一章就睡。”我头也没回,声音干涩而稳定。
门合上了。那一刻,我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碎裂的声音。这就是我的“矛盾”:我痛恨这种欺骗,痛恨自己在网课上烧钱却在游戏里虚度,但我更贪恋父母眼中那个“懂事儿子”的幻影。我是一个卑劣的演员,在名为青春的舞台上,领着我不配得到的片酬——那份毫无保留的爱。
那杯牛奶放在桌角,热气氤氲。我拿起来抿了一口,放了回去。牛奶一会儿便在液面结出一层皱缩的膜。我重新切回游戏,看着空荡荡的星琼余额,突然觉得一阵巨大的空虚,像黑洞一样吞噬了所有的兴致。
…………
“We are all in the gutter,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.”
王尔德这句话像一句古老的谶语。我身处沟渠,满身泥泞的矛盾:一边是无法自控的堕落引力,一边是清醒过后的自我厌弃。而我的星星,囚禁在那块 4.4 英寸的手表屏幕里。
我想起她。
我和她的关系,就像这层奶膜。看似融洽亲近,实则我不属于液体,也不属于空气,我只是悬浮在中间的、那层尴尬的半固态。一触即破,却又真实地阻隔了一切。
在那些被试卷填满的日子里,她是我唯一的“日记本”。我向她输出着关于这个世界的只言片语,不仅是为了倾诉,更是为了在脑海中构建她在那块小小的屏幕后,眼角下垂、嘴角上扬的弧度。
我会转发刷到的视频,告诉她物理老师的幽默;我会吐槽化学老师奇奇怪怪的口音;我会分享生物老师和老班那些离谱又令我无奈的要求;我会炫耀崩铁里偶尔出现的小保底,或者分享我觉得哪个角色好看……她是一个合格的观众,总是回复一串“哈哈哈”,几个表情包,和一些评论。我能透过冰冷的像素,看见她眼角微微下垂,嘴角上扬,这是她独特的、带一点狡黠的笑。
……
“这个电解池怎么看?阳极是谁先放电?俩膜中间溶质浓度咋变?”
有一天晚上,她发来一张图片。图拍得有点歪,光线昏暗,像是一张来自遥远星球的求救信号。
我把图片放大,在草稿纸上重新画图。我很擅长这个,画出整齐的烧杯,标出阴阳极,画出电子流动的箭头,像是在不知名的战场上排兵布阵,守护着某种秩序。
“阳极是氯离子放电,”我在手表那令人抓狂的小键盘上,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,像是在发送摩斯电码,“因为溶液里离子的放电顺序……”
第二天课间,你拿着卷子走到了我的座位旁。
这是极其罕见的时刻。你站在我左边,大概只有三十厘米的距离。那个距离,近得让我产生了一种嗅觉上的幻觉——我不确定那是你发梢洗发水的柠檬香,还是试卷上新印的油墨味,亦或只是我心跳过速时,大脑为了留住这一刻而编造的信号。
我坐在座位上,不敢抬头太高,只敢盯着题目。
“这儿,你看,”我指着中间那条竖线,“这是离子交换膜。容器中溶液要保持电中性,所以钠离子要穿过膜往中间移动……”
你蹲下来了一点,凑近看我的笔尖。
“哦——懂了!”你眨了眨眼,突然转过头看我,双眼睁大,露出了一个毫无防备的、像小猫般得逞的笑容。
那一刻,周围嘈杂的打闹声、后排男生拖动椅子的刺耳声,全都退潮般消失了。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这感觉不像汽水被拧开的喧哗,更像是深夜戴着耳机听歌,突然切到了一段极安静的钢琴独奏。我知道这旋律转瞬即逝,马上就会被下一首摇滚淹没,但在那一秒,整个宇宙只剩下这个频率。
我强装镇定地避开你的目光,继续给你讲解。我用力地控制着我的耳朵,试图用理智给毛细血管降温,可最后它们依旧无可挽回地热烫起来。
……
大概二十天前,临睡之际,手表震动了一下。
“生日快乐!给你买了礼物,明天带给你。”
屏幕上的字光很亮。我愣了一下,看了一眼日历——离我的生日还有整整二十天。
那一刻,我的内心竟出奇的平静。这很像一道化学平衡题:搞错日期代表着“不上心”,这甚至在我对她的预期之内;而提前买好礼物又代表着某种程度的“上心”。正负相抵,净反应热为零。我没有难过,也没有特别高兴,只是平静地指出了她的错误。
但第二天,当两个小盒子真切地被她递到我手上时,我筑起的理智防线还是瞬间崩塌了。
因为我的生日总是在寒假,接近过年,这十八年来,我习惯了同学们回家过年、无人记得的冷清。
可此刻,手里沉甸甸的重量在提醒我:这一刻,我被记得。
更重要的是,送礼物的人是她。哪怕她记错了日子,哪怕这只是同学间的礼尚往来,但在那一秒,我确实感受到了被她在乎的窃喜。
…………
然而,题目有标准答案,感情却没有。
其实我早就知道。我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。
我可以是她最信任的“解题机器”,可以是她无聊时的“电子树洞”,但绝不会是那个能让她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人。
我对此心知肚明,但我还是会在你问“为啥”的时候,认认真真地画图、解释。哪怕我知道,我永远只是你生命里的“参考答案”,而不是那个充满变数与心跳的“主观题”。
电解池的那道题,核心考点是“隔膜”。
离子交换膜允许离子通过,自身不能溶解,不能与电解池内任何物质反应。
我就像那张膜。为了维持整个反应体系的平衡,我必须允许信息的穿梭,允许友情的通过,但我永远被固定在原地,阻挡着原本可能发生的、更亲密的分子层面的融合。
我在放弃与坚持的拉锯战里反复横跳,像极了我在游戏里那非酋的手气——明知大概率是徒劳,却总存着万一的侥幸,在虚无中等待奇迹。
不知何时,窗外的城市已经睡去。远处的路灯昏黄,像一颗融化中的橘子糖。
“We are all in the gutter,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.”
王尔德说这话的时候,一定没想过,有时候仰望星空的人,本身就深陷沟渠,而且脖子还很酸。
…………
零点的钟声敲响了。
屏幕上的光标在闪烁。我的十八岁,就这样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二凌晨降临了。
没有礼炮,没有蛋糕,只有一杯凉透的牛奶,和满屏未解的数理化题目。
我想起游戏里卡芙卡说的那句话:“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,不要让自己后悔。”
后悔吗?
后悔没在刚才那一抽里更虔诚一点?后悔这无数个夜晚里,在父母的信任和自我的放纵之间反复横跳的卑劣?还是后悔寥寥几字从未说出也无法说出?
……
我不知道。得与失在我身上表现得如此割裂:我用从不缺席的高分,粉饰着那个在社交频道里总是缺席、像老式接收器般信号延迟的灵魂;我用日复一日的完美表演,换取在深夜沉溺于虚拟的特权,却又要独自吞咽清醒后成倍反噬的自我厌弃;我死守着“最佳损友”的安全区,用无数次的答疑解惑去博取那万分之一的侥幸,以此掩盖——在名为恋情的卡池里,我从始至终都只是个陪跑的局外人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,切断了我的自怨自艾。
不是她。
是那个“咱们仨”的兄弟群。
[DJ. He]: “生日快乐!”
[幺儿]: “好大儿生日快乐!”
[幺儿]: “哦对,我最近开始研究暑假去哪玩了”
[幺儿]: “你前面不是催得紧吗?目前我计划是这样:……”
看着这些文字,我鼻头微酸。
我总是觉得自己“脱节”,是个不懂新梗、慢半拍的“老式接收器”。但神奇的是,总有那么几个特定的频道,永远向我开放。他们不需要我秒懂每一个梗,也不在乎我是几G网速。在他们面前,那个“不完美、有点非酋”的我,是被完全接纳的。
此岸有遗憾,但此岸亦有兄弟。
[我]: “你就好好搞你的旅行安排,我来负责装备与技术支持就行”
[我]: “要不把旅行录下来吧?回来做成vlog”
[DJ. He]: “OK啊”
[幺儿]: “可”
[我]: “感觉我们需要一个大疆Osmo Pocket 3,以及……”
[我]: “哦对,最重要的一点:不准临阵脱逃!”
[DJ. He]: “废话”
[幺儿]: “废话”
[幺儿]: “包来的啊”
……
我站起身,推开阳台的门。骨骼在静夜里发出轻微的爆鸣,那是身体悄悄生长的声音。
凌晨的城市显露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寂静。远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光晕开在潮湿的空气里,和路灯相互映衬,变成大大小小的橘子糖。我撑在栏杆上,铁锈的颗粒感透过袖口传来。这座小城睡得很沉,路灯的光浮在低空,照不见太高处。
风吹过来,带着点泥土腥气和早餐铺煤炉刚生火的烟火味。
她就住在这片光晕的某一点上。也许正睡得香甜,也许还在打语音。
我和她的对话框停在那个白色的“谢谢”气泡上,像一个小小的、圆满的句号。
也好。有些故事不需要转折,有些心事,适合永远只是心事。
就像我知道电解池里,电子永远只能在导线上奔跑,永远无法游过溶液一样。有些界限是物理性质决定的,不是靠努力就能打破的。
“从现在起,一切归零;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。”
这句话突兀地浮现在脑海里。
归零不是遗忘,不是把过去那个沉迷游戏、暗恋无果、虚伪表演的自己杀掉。而是承认。
承认那就是我。承认那一百五十抽的沉没成本,承认那段无疾而终的悸动,承认我在沟渠里挣扎的姿态并不优美。
因为只有承认了这些,我才是我。
十八岁的意义,不在于突然变强,而在于终于敢直视那个并不完美的自己。浪漫主义不是逃离现实的致幻剂,而是看清了生活的沟渠后,依然愿意擦干净脸上的泥,抬头看看天亮没亮。
天边真的泛起了一层鱼肚白。那是很淡的青色,像被水洗过的旧牛仔布。
…………
我回到房间。
桌角的牛奶已经彻底凉透,那层膜完整得像一面小小的鼓,封存了昨夜所有的浑浊。
我端起杯子,仰头喝了两口。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,带着腥气。那层一直困扰我的膜,在重力的作用下瞬间破碎,黏在杯壁上,狼狈不堪。
冷了的牛奶确实不太好喝。但至少,它的味道,热的冷的,我都尝过。
我走向卫生间。
水龙头拧开,水流激荡。剩下的乳白色液体旋转着被卷入下水道的漩涡,连同那些纠结、那些小心翼翼的试探、那些无法言说的秘密,一起消失在黑洞洞的管口。
一切都干净了。
洗净杯子,倒扣在沥水架上。晶莹的水珠顺着杯壁滑落,“滴答”一声,轻得像一声叹息,又像一声发令枪。
我回到书桌前,关掉了还在后台运行的游戏窗口。没有犹豫,也没有那种名为“发誓再也不玩”的虚假仪式感,只是平静地点击了红叉。
然后,我摊开那本只写了几页的化学错题集。
我翻过那些写满潦草字迹的旧页,翻到崭新的一页。刚好第十八页。
台灯的光打在纸面上,白得微微反光,像一片未被踩踏过的雪地,又像一个等待被定义的黎明。
我按动中性笔出芯,“咔哒”一声。
声音清脆,在寂静的深夜里,像是一声孤单的电报音。
若是以前,我会害怕这声音太轻,会被世界的喧嚣淹没。
但现在,我只是笑了笑。
我不需要去追逐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宏大信号,也不必为了一时的“脱节”而恐慌。
因为我知道,就在这声“咔哒”的频率里,在那个乱七八糟的群聊里,在那些真正属于我的频道里——
总有人在听。
我握紧笔,手腕压在纸面上,感受到纸张纤维微弱的反作用力。
笔尖落下,黑色的墨水抱住滚珠。我向它行注目礼,目睹它在纸面正中央切开第一道竖线,那是“电”字的起笔。
接着却回到开端,划出横线,似从头再来,却又实与第一笔紧密相连——似在书写一个新的故事。
短横、长横、再是那道蜿蜒的竖弯钩……笔触摩擦纸面,发出细密的沙沙声,那是十八岁的第一行字:
“电解池与原电池的异同、多池多室装置分析。”
墨水迅速渗进纸张粗糙的纤维里,洇出一丝细微的毛边,留下清晰的、黑色的、不容修改的痕迹。
我盯着这行墨迹,看着它在纸上缓慢晕开,仿佛生出了细小的、墨色的根。
它会就此长成足以遮蔽风雨、将我所有的残缺都开成圆满的参天巨木吗?
—— 不。不会。
—— 毕竟它什么也不是。
它既不是能解开人生难题的定理,也不是能兑换未来的标准答案。
它只是一个开始。
一个序章的开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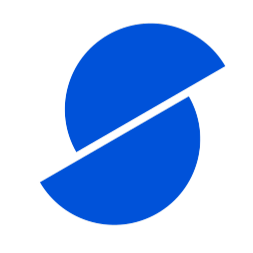 Spixed's Blog
Spixed's Blog Spixed
Spixed